
《人类学学报》

马歇尔·萨林斯对西方文明的人类学反思
20世纪70年代,法国人类学家路易斯·杜蒙(Louis Dumont,1911—1998)在一场演讲中提出:我们(西方社会科学)的定义和概念很大程度上来源于我们自身的现代文化,即使人类学的经验或多或少对其有所改变……因而我们目前的定义表达了我们自己的文化,而我们自身的文化(也就是我们自己的意识形态)体现了一种特殊的发展。杜蒙的这段话建立在他对世界文化多样性的人类学式清醒认识基础上,是其对自身所处世界作出的重要反思:作为当时世界领头羊的西方文明,只是世界诸文明的一部分。因而源起于西方文化的话语体系,只是从这种特殊文化中发展出来的、仅能体现西方文明的一些定义和概念。此后,杜蒙的观点在人类学界成为一种共识,西方社会科学界尤其是人类学界对自我的反思一直在延续,而将这种反思进行得最为深入彻底的,非美国人类学家马歇尔·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1930—2021)莫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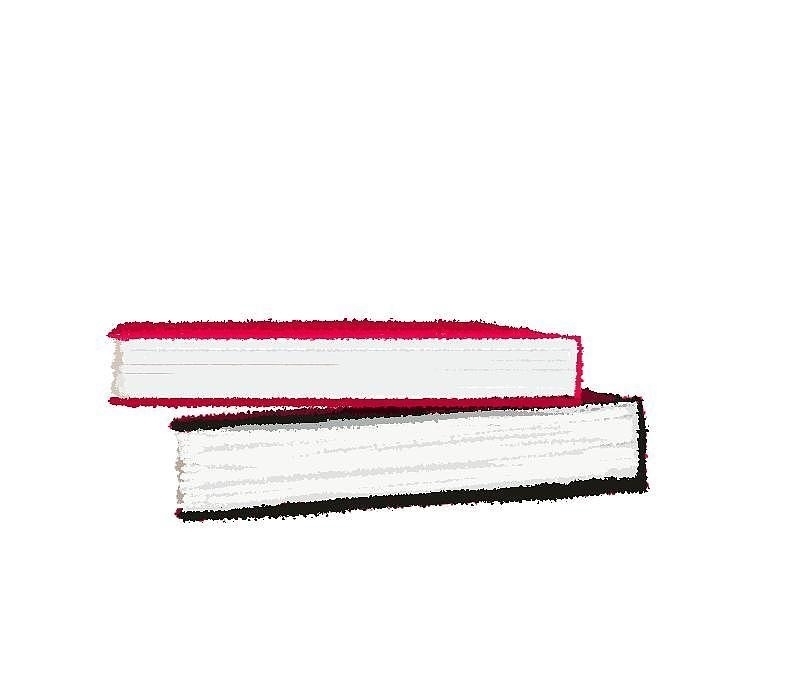
经济活动是一种文化行为
马歇尔·萨林斯,美籍犹太人,是文化研究领域跨世纪的著名学者,被结构主义大师列维-斯特劳斯称为“人类学家中的圣人”。他师从美国著名新进化论学者怀特,深受后者将文化确定为一种象征性构成的秩序观念的影响,终其一生致力于文化研究。通过对他者的研究反观自身,是整个人类学学科的学术目标,更是萨林斯一生学术轨迹的写照。萨林斯的田野研究对象是太平洋诸岛的土著,然而,田野参与式民族志著述并非萨林斯的长项,他的影响力在于基于民族志资料的理论探索。萨林斯一生著述颇丰,现已出版的著作有19本,文章达100多篇,从这些作品中可以看到他学术发展的历程。伴随着他一生丰富多样的研究主题(经济制度、王权理论、亲属制度、自然与文化、文化与实践的关系、全球化理论中的文化变迁等),萨林斯的理论主张经历了从技术决定论的新进化论向文化决定论的转变,这一转变也决定了他对社会生物学和资本主义经济理论等学科主张的批评,尤其是对其背后功利主义思想深入骨髓的批判。在这些批判之下,萨林斯想要做的是将西方人类学或者说西方社会科学的认知范式彻底打碎,寻找一种更为去中心化的学术研究范式。
萨林斯对西方社会科学开战,始于他的《石器时代经济学》一书。这部发表于1972年的作品,实际上是他整个20世纪60年代思考的结晶。60年代的萨林斯一边作为激进的左翼行动者,积极参加反越战等社会活动;一边作为人类学者,出版了《文化与进化》《摩拉:一个斐济岛上的文化与自然》《部落人》等带有鲜明进化论色彩的作品。经过20世纪50年代英美人类学界有关社会与文化的大论战之后,美国的人类学将文化确定为学科研究对象。20世纪50—60年代的美国人类学界,将文化研究与进化论结合起来,开创了一门被称为新文化进化论的新理论。该理论认为社会文化的发展形态是适应自然生态的结果,因此社会文化研究应与自然科学相结合,统计模型、量化等被引入文化研究中,文化生态学成为当时的一门显学。萨林斯早期的研究皆属此列。然而,萨林斯并未在该领域长久停留,他很快就被卡尔·波兰尼的经济学理论所吸引,并将之引入人类学的分析当中。从文化生态学到经济人类学的转变,有着内在的一致性,因为两者都关注劳动、土地、分配、交换等被马克思称为经济基础的东西。如果说卡尔·波兰尼为了论证自身观点大量利用了人类学的土著社会材料,那么由人类学开展一种卡尔·波兰尼式的经济人类学研究就会更有说服力,因为人类学家观察任何一个土著社会都能看到:经济是深深嵌入在其他社会结构当中的,并不存在一种独立体系的自由市场,生产与交换交织在其他社会结构尤其是亲属制度当中,并深受后者的制约和影响。也就是说,在人类历史上,嵌入式经济是常态,自由市场经济是一种变异。这就是萨林斯在《石器时代经济学》中提及的经济学理论的实质论。秉持这一观点,相对于物质极大丰富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萨林斯提出了“原初丰裕社会”概念,试图以此为狩猎采集社会正名。也就是说,我们对于狩猎采集社会“贫瘠落后”的印象,其实是一种误解,狩猎采集社会实质上是一种劳动效率高、闲暇时间充裕的生活状态;从劳动时间和产出比来看,现代资本主义才是一种效率低下的生产方式。
基于以上观点,萨林斯重新定义了经济:经济活动并不仅仅是人类的理性选择,它实际上是一种文化行为,经济理性逃脱不了意义体系的约束。为了更加充分地探讨经济行为中文化与理性之间的关系,同年,萨林斯又出版了《文化与实践理性》一书。在该书中,他再次旗帜鲜明地提出上述观点,批判那种认为文化是个人在追求自身最大利益的理性活动中形成的功利主义观点,主张一种象征或者意义理性。虽然萨林斯并没有因为主张文化决定论,而完全忽视自然生态的作用,但是他认为自然生态的基础性作用需要进入文化系统中才能开始运行,因此首先是由文化来选择自然事实。20世纪60年代中期,法国结构主义大师列维-斯特劳斯的作品犹如一记响雷炸裂于美国人类学界上空,萨林斯也对这一来自法国的新思想作出了积极回应。他迅速显现出对结构主义的着迷,并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前往法国跟随列维-斯特劳斯学习结构主义。这段经历对他后来试图发展结构与历史的理论有着重要影响,而利用结构主义来分析象征和意义系统,则是萨林斯后来研究中最重要的一环。同时,作为少数有勇气在60年代与马克思对话的美国学者,萨林斯在书中回应了当时马克思主义与结构主义之间的争论,他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马克思主义分析框架需要面对的问题是:如何分析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尚处于同一个结构中的土著社会。但在他看来更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与结构主义有着重要的共同点,即都强调实践中的文化,也就是说都关注生产实践与象征秩序两者的关系问题。因此,打破功利论,强调文化论,是萨林斯的真正目的。这些探讨的背后,萨林斯认为他最高的目标是帮助那些尚未觉醒的人逃脱他们自制的经济决定论牢笼。